1、关税壁垒下的国产射频崛起:昂瑞微等国产射频前端公司IPO冲刺正当时
2、传英特尔将裁员超20%
3、智路资本拟30亿美元出售新加坡封测厂联合科技
4、高管揭秘比亚迪欧洲困局:经销商拓展不足、领导层不熟悉市场
5、特朗普松口:对中国145%关税过高,将大幅下降
6、欧盟数字法开出首张罚单:苹果和Meta合计被罚7亿欧元
7、转移生产线成本过高 美企:深度依赖中国工厂
1、关税壁垒下的国产射频崛起:昂瑞微等国产射频前端公司IPO冲刺正当时
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半导体关税壁垒,意外催生了国产射频前端产业的黄金发展期。自中美双向加征关税以来,中国手机品牌厂商的供应链安全焦虑持续加剧,这种战略需求直接转化为对国产射频器件的采购倾斜。国产射频企业凭借贴近客户的地缘优势、灵活的定制化服务以及显著的成本优势,即将迎来第二波国产替代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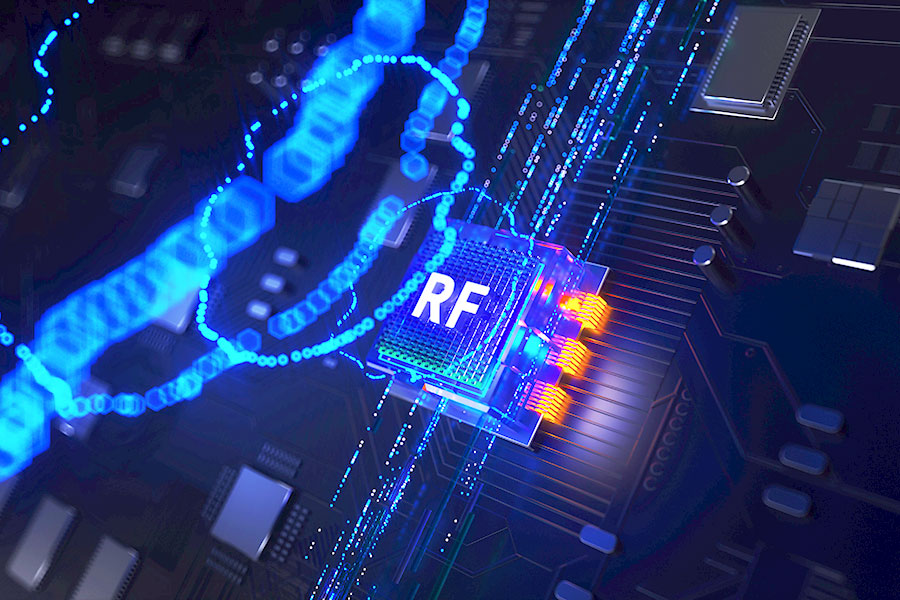
一、国产替代加速器效应显现
在特朗普政府挥动关税大棒,将对中国关税上升到创人类历史的245%的时候,恐怕没有关注到,Skyworks、Qorvo等晶圆、滤波器产地在美国的芯片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已被推向了困境。例如,美国射频巨头Qorvo财报显示,其中国区营收占比已从2019年的36%降至2023年的19%,市值缩水超4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射频前端头部企业VC模组出货量突破1.2亿颗,2024年度昂瑞微5G PA及模组营收占比达总体规模的42.96%,增速明显。
除传统的关注赛道,例如智能手机、IoT通讯模组外,智能汽车的国产替代需求在此次关税战中站到了前沿阵地。原本近2千万的车载NAD(Network Access Device),支撑起中国汽车万亿赛道的基础网联设备,也即将迎来一波国产替代。Skyworks、Qorvo最后的阵地即将被国产车规方案替代。例如VC、昂瑞微等具有全套车规射频前端解决方案的国产公司即将发起第二波国产替代的号角。有能力、有布局、有经验,国产射频前端厂商在车规市场发力并非空穴来风。
二、资本市场的强力助推成为关键变量
昂瑞微上市申请获受理,飞骧、锐石先后启动上市辅导,形成“技术突破-规模量产-资本加持”的良性循环。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国产射频企业合计融资超45亿元。卓胜微Fab-lite模式投入近百亿,且在资本市场持续融资数十亿,行业发展空间仍然巨大,需要资金加持,加速国产企业发展,加速国产替代。高端模组的突破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解决高端滤波器及模组的加速迭代。
这场由关税壁垒引发的产业变局,正演变为重塑全球射频格局的结构性变革。国产厂商在射频前端模组等核心器件持续突破,射频前端的进口替代已从政策驱动转向技术驱动。具备全栈研发能力的中国射频企业,争取在5.5G和6G时代,与国际领先公司并驾齐驱,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2、传英特尔将裁员超20%
据知情人士透露,英特尔公司本周将宣布裁员20%以上的计划,旨在消除这家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的官僚主义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
知情人士称,此举是精简管理层、重建工程驱动型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这将是英特尔上个月上任的首席执行官陈立武(Lip-Bu Tan)上任后的首次重大重组。
此次裁员是继去年8月宣布裁员约1.5万人之后,英特尔再次宣布的裁员计划。截至2024年底,英特尔员工总数为10.89万人,较上一年的12.48万人有所下降。
陈立武的目标是扭转这家标志性芯片制造商的颓势,此前英特尔多年来一直被竞争对手蚕食市场份额。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公司失去了技术优势,在人工智能计算领域难以追赶英伟达。这导致该公司销售额连续三年下滑,亏损不断扩大。
陈立武曾担任Cadence的资深高管,他誓言要剥离英特尔非核心资产,打造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上周,英特尔同意将旗下可编程芯片部门Altera的51%股份出售给银湖管理公司(Silver Lake Management),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一步。
陈立武上个月在英特尔愿景大会上表示,英特尔需要填补失去的工程人才,改善资产负债表,并更好地调整制造流程以满足潜在客户的需求。
该公司定于周四公布第一季度业绩。
3、智路资本拟30亿美元出售新加坡封测厂联合科技
据知情人士透露,智路资本正在考虑出售新加坡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公司UTAC Holdings Ltd.(联合科技)。
知情人士表示,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募股权公司已聘请了一名顾问,并可能寻求在潜在的出售中筹集约30亿美元资金,目前这一考虑仍处于早期阶段。
2020年,智路资本从Affinity Equity Partners和TPG Inc.等股东手中收购了UTAC。
该公司网站显示,UTAC在总部新加坡、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设有生产设施,销售网络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亚洲。
智路资本网站介绍,该公司是一家全球化的专业股权投资机构,公司专注于半导体核心技术及其他新兴高端技术投资机会。智路资本的投资人包括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大型金融机构和家族基金等。
4、高管揭秘比亚迪欧洲困局:经销商拓展不足、领导层不熟悉市场

据报道,中国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六位现任和前任高管表示,该公司正在彻底改革其欧洲业务,此前该公司出现了一些战略失误,包括未能签约足够多的经销商、聘请不够了解当地市场的高管,以及未能在抵制全电动汽车的市场提供混合动力汽车。
这些高管称,比亚迪迅速采取行动,解决了在这个关键出口市场的早期问题,大幅扩大了经销商网络,并提供了丰厚的薪酬,从欧洲汽车制造商那里挖走高管,尤其是Stellantis。
比亚迪2024年12月宣布,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将对其欧洲战略至关重要。此前,比亚迪欧洲特别顾问阿尔弗雷多·阿尔塔维拉(Alfredo Altavilla),他也是比亚迪重启欧洲业务的关键高管之一,曾向比亚迪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传福建议,纯电动汽车战略在许多欧洲国家仍然难以推广。
阿尔塔维拉表示:“他很快就收到了信息,并向比亚迪的工程师们反馈,每款新车型都必须同时提供电动版和混合动力版,以应对欧洲市场的需求。在绿色转型方面,对消费者进行教育至关重要。”
据报道,比亚迪已聘用了一些欧洲高管,并公开承认其在德国市场存在问题。这是比亚迪内部高管首次详细披露其发现的问题以及公司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系统性措施。由于涉及敏感的战略问题,大多数高管均要求匿名。
2024年 12 月,阿尔塔维拉在意大利宣布,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将成为比亚迪未来欧洲战略的核心,并表示,如果只提供电动汽车而违背消费者的偏好,那将是“愚蠢的”。
比亚迪2024年6月首次与菲亚特-克莱斯勒前高管阿尔塔维拉接洽,并于8月宣布任命。阿尔塔维拉此前曾担任私募股权公司CVC Capital Partners的高级顾问。
阿尔塔维拉则从Stellantis挖来了数名冉冉升起的明星经理,包括负责德国及其他几个中欧国家业务的玛丽亚·格拉齐亚·达维诺 (Maria Grazia Davino)、负责意大利业务的亚历山德罗·格罗索 (Alessandro Grosso)和负责西班牙业务的阿尔贝托·德·阿萨 (Alberto De Aza)。比亚迪一位现任高管表示,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为他们提供了大幅加薪和“成长机会”。
一位熟悉比亚迪挖走的高管工作的 Stellantis 消息人士表示:“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些人。”
期望值过高
比亚迪决心迅速加强其欧洲业务的另一个迹象是,该公司去年任命其二号人物李柯(Stella Li)负责欧洲业务。
她取代了比亚迪前欧洲业务CEO舒立克(Michael Shu)。舒立克曾预测,比亚迪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匈牙利的首家欧洲工厂投产之前,将占据欧洲电动汽车市场至少5%的份额。然而,截至2024年,比亚迪的市场份额仅为2.8%,总销量仅为5.7万辆,低于公司预期。
比亚迪在欧洲发展的迫切性部分源于其在中国市场销量飙升的记录。自 2020 年以来,比亚迪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增长了 7 倍,预计到 2024 年将达到 420 万辆。比亚迪超越特斯拉,2024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现在是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还面临着争相进军欧洲市场的中国竞争对手,包括奇瑞、吉利、小鹏汽车、长安等。所有中国汽车制造商都面临着在海外市场增长以提高利润的压力,但由于众多电动汽车品牌之间旷日持久的价格战,中国汽车制造商很难维持利润。
比亚迪的合作伙伴和行业专家表示,比亚迪已经认识到其在欧洲存在的问题,并果断采取行动解决这些问题。
Ayvens CEO Tim Albertsen 表示:“他们对此非常重视,但他们需要明白,在欧洲建立地位需要时间。”该公司是欧洲最大的租赁公司之一,也是比亚迪在该地区合作伙伴。“就像欧洲或美国汽车制造商进入中国一样,中国人在中国做得好的事情,在欧洲不一定能奏效。”
早期迹象表明,比亚迪重启欧洲市场正在取得成效。比亚迪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市场的销量在2025年第一季度增长了两倍多,达到3.7万多辆,而2024年第一季度仅为8500辆左右。
研究公司 JATO Dynamics 中国区经理 Bo Yu 表示,比亚迪在中国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快速发展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例如,比亚迪今年 2 月通过免费向其所有产品线(包括售价低于 10,000 美元的车辆)提供“上帝之眼”辅助驾驶技术,击败了中国竞争对手。
在本周的上海车展上,比亚迪展出了四个不同品牌的大型汽车,其规模之大令大多数其他汽车制造商相形见绌。该公司推出的新车型涵盖了从入门级的海豹06(起售价约为人民币10万元)到海狮06(起售价约为人民币16万元)的车型,再到超豪华三排座SUV——仰望U8L,以及高端跑车概念车——腾势Z。
缺乏对欧洲市场了解
在中国市场迅速崛起后,比亚迪于2023年雄心勃勃地进军欧洲市场。比亚迪前欧洲业务负责人舒立克2024年5月表示,比亚迪的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
但现任和前任管理人员表示,比亚迪事先未能研究欧洲市场。
例如,比亚迪斥资高调赞助了德国2024年欧洲杯足球赛。当时,比亚迪宣称自己是德国排名第一的“NEV”(新能源汽车)制造商。“NEV”在中国通常用来指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但对德国消费者来说,这个缩写毫无意义。
比亚迪内部人士称,比亚迪最初的经销商网络规模太小,而且过于集中于大城市。
比亚迪德国业务前 Stellantis 经理达维诺 (Davino) 今年 3 月表示,比亚迪计划将德国的经销商网络从 27 个扩展到 120 个。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2024年销量达280万辆。比亚迪预计2024年在德国的销量不到2900辆。“在德国市场发展不容易,”达维诺说,“这里仍然缺乏一些基础。”
比亚迪前任管理人员表示,该公司在进军欧洲市场之前的核心错误是将其视为一个单一市场(如中国或美国),而不是几十个不同的国家。
比亚迪一位前经理将欧洲各国市场比作“锅里的青蛙”,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跳跃,并补充道:“比亚迪现在才开始明白这一点。”
5、特朗普松口:对中国145%关税过高,将大幅下降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4月22日)表示,他不会与中国进行“强硬”的贸易谈判,这是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美国与北京的长期贸易战不可持续数小时后。
Scott Bessent周二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的对华关税战将因对经济的潜在影响而很快降温,并预测中国关税将调整,从而提振了股市。
“145%非常高,”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谈到当前对中国产品的最高税率时说,“不会那么高,会大幅下降,但不会是零。”
这些报道的评论帮助推动华尔街股市飙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周二均收盘上涨至少2.5%。
Scott Bessent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尽管在螺旋式上升的贸易战中,与北京的谈判尚未开始。
据报道,Scott Bessent声称,目前美国和中国在互征关税达到美国产品125%和中国商品高达145%后,实际上已经实施了贸易禁运。
4月9日,特朗普暂停了对除中国外所有其他国家的一系列互惠关税90天,这一暂停旨在为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达成一系列一对一贸易协议留出时间。
6、欧盟数字法开出首张罚单:苹果和Meta合计被罚7亿欧元
欧盟《数字市场法》开出首张罚单。
当地时间4月23日,有外媒报道称,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出严厉报复警告之后,欧盟对苹果和Meta开出了相对温和的罚单,对这两家公司因违反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反垄断新规总计罚款7亿欧元。其中,欧盟监管机构根据《数字市场法》对苹果公司处以5亿欧元罚款,对Meta罚款2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要求苹果取消对开发者的技术和商业限制,苹果不允许开发者绕过其应用商店在其平台市场之外进行销售。Meta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无广告服务商业模式也违反了数字市场法。外媒报道称,欧盟委员会仍在评估Meta未来数月为欧洲用户提供的不付费版本中,看到“个性化程度较低的广告”的选项是否符合停止令。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欧盟根据《数字市场法》开出的首张罚单。根据该法案,监管机构有权对一家公司处以高达其全球年收入10%的罚款。两家公司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盟的决定,否则将面临进一步罚款的风险。“这一惩罚力度远低于传统欧盟竞争法下的惩罚措施。”外媒报道指出,罚款约相当于每家公司年收入的0.1%。
“苹果和Meta未能遵守规定。”欧盟反垄断负责人Teresa Ribera表示,“所有在欧盟运营的公司都必须遵守我们的法律并尊重欧洲的价值观。”
公开资料显示,《数字市场法》是欧盟在2023年针对科技巨头颁布的打击垄断行为的法规之一,旨在通过遏制大型科技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行为,确保消费者在使用网络服务时有更多选择,于2024年3月7日正式生效。
苹果已经表示将就此提出上诉,认为欧盟委员会的要求不利于保护用户隐私和安全,迫使苹果免费交出技术。Meta表示可能会上诉,认为欧盟委员会强迫Meta改变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对Meta征收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同时要求我们提供劣质服务。”
7、转移生产线成本过高 美企:深度依赖中国工厂
美国总统特朗普企图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但绝大多数美国中小企业表示,仍深度依赖中国工厂,产线转移回美国的成本太高所以非常困难。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基辛格并认为,苹果公司(Apple)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生产iPhone,这需要几十年的沉淀。
美国科技媒体WIRED近日调查10多位美国企业老板,包括电子设备商、床垫、时尚品牌创办人等,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是全球制造业标杆,无论关税多高,想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非常困难。
首先,成本是企业选择中国制造的重要因素,低价不等于低质量。第二,中国是全球工业机械生产的领导者,工厂能灵活调整设备满足客户多变的需求,快速应对小批量制造与客制化需求。第三,不少美国企业老板表示,一些产品只能在中国找到;第四,庞大的产业集群与完善的上下游协作能力,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复制。
此外,美国企业尝试转移产线时,也难以突破原料、技术与人力瓶颈。某家皮包企业创办人表示,尽管越南可代工生产部分产品,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中国技师手中,即使回流美国,也会受制移民政策无法引进技术人员来搭建生产线。
对于苹果能否将iPhone带回美国生产,基辛格表示,“实际的情况是,你必须先在某个地方建设厂房,然后在附近设立塑料公司,然后是电阻器公司,再来是显示器公司,要逐渐形成供应链“一条鞭”的科技聚落,这过程要耗上数十年的时间。”
基辛格强调,转移供应链需要成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沉淀,“供应链不会因为你要求就回归,如果回归也是因为你创造了经济激励、资本和能力来推动他们回归”。(工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