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开年, DeepSeek的横空出世 让大众再次拓宽了对AI技术的想象, 其背后的公司深度求索也引发了大量好奇与关注。 据报道, DeepSeek团队大多为清北应届生、在读生, 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
一条对话了3位正在AI行业工作的00后, 发现这一行业中正在发生着全新的工作模式迭代: 他们团队年轻,成员精简, 二十出头就能独当一面, 大多来自名校,包容不同专业背景, 写代码、回邮件、写方案、作图都可以分给AI完成。
他们也重新定义着能力和话语权的新标准: 不像传统互联网一样追求垄断, 而是更多地碰撞、交流, 不再以大厂“职级”论长短,而是让“作品”说话。
初高中生入局,让我有了紧迫感
孙东来Sidrel 01年 杭州
研一学生 AI公司创始人&CEO

去年8月,孙东来第一次参加黑客松
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在全职创业中。
我们团队现在在做的事是我在西湖边散步的时候想到的,我突然在想,能不能用AI把我的梦境记录下来。当时我朋友也是长期记梦者,我们一拍即合,当场编辑了篇帖子发到了小红书上,一下子就爆了,三天浏览量达到了20多万,5千条评论。
因为明确了需求,我们就正式开始组建团队。我是后端开发兼产品,再加前端、设计、营销,总共四个人就开始做了。

用户在孙东来团队开发的梦境社交软件Dreamoo上记录的梦境,目前他们已拿到种子轮投资,估值3000万
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在app store公测了一个月,记录了三千多个用户的梦境。它是一款可以记梦、绘梦、解梦的社交App。大家可以让AI帮你将自己的梦境用图片的形式记录下来,与AI解梦师对话,也可以通过分享来结交同频的人。设想一下,你早上起来发现平台给你推了一个昨天晚上跟你做一样梦的人,这件事还是挺有趣的。
人一天只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清醒的,睡觉的8小时我们根本不记得做了什么。所以我很想知道,也想记录那被我们遗忘的三分之一人生,建立全球最大的梦境世界。

24年底,浙大脑科学专业的博士加入后,在联合国总部分享了团队创作的产品
我成长的环境跟创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就好像家里的基因突变一样,因为我本身就有非常多的点子,如果我不做创业这件事,这些点子它只能是点子,每天就是想出来,然后消散掉。所以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把点子转化落地?
比如从本科的时候开始,我就会参加一些创赛、挑战赛之类的比赛,当时做的是Web3的项目。读研之后,我们专业的研究生是偏向授课制,无导师的,研一是学一些基础课程,你也可以自由地去找实验室的导师,但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在实验室里做科研,反而更喜欢出来做自己的项目。

凌晨3点的黑客松会场
真正创业的起点始于去年8月份,我参加的第一场黑客松 (hackthon,一群工程师在期限内设法完成指定内容的聚会活动) 。
那场黑客松,给大家自己操作写产品的环节大概就三天,我记得那3天我就睡了8个小时。所有人都在熬夜,晚上睡得横七竖八的,有直接睡地板上的,直接睡楼道上的,也有直接睡椅子上的。
我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多在做同样事情的人,大家为自己的产品都非常拼命。这也是我第一次跟AI有了比较深度的接触,因为当时有很多的AI公司参加,也有很多教我们如何使用AI工具的workshop可以去参加。
黑客松这种活动有点像一个创业者的厨神大赛,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现出你的菜来,然后会有投资人作为评委来尝你的菜。有时候跟你做出了什么菜也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还是看你如何在极限的时间里,利用有限的资源烧出菜来,这是创业者自己的特质。
进入创业圈之后,我会有一种担惊受怕的感觉,因为厉害的人太多了,感觉不努力就会随时被别人追上。
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比如我参加的这个黑客松,叫AdventureX,完全是一群高中生自发组织的一个团队,拿到了100万的投资,这个五六天的营里面,很多初中生都已经开始做项目,并且能赚钱了。

和团队参加S创上海2024科技创新大会
大家刻板印象里的“00后整顿职场”,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做的工作,他们自己不喜欢或者觉得无意义,所以拒绝无效的加班。像我周围的人,都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通过创业这件事快速成长,认识不同的人。
我工作起来也比较肝,没什么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也写代码到两三点。自己生的娃,你不能说到休息日了就不管它了。
有人会说现在是在进行一次工业革命,你不会像今天一样觉得AI能离我这么近。比如最近大火的Deepseek,大家之前很难想象AI可以这样丝滑地融入到生活当中的,就像一个能随手使唤的秘书一样。
在这个节点,AI领域还没有形成大厂垄断的格局,大家都在发散自己的思维,都在找什么东西是最后会收束的。对我们初级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放弃传统上升路径,拥抱不确定
晨然 99年 上海
AI公司全栈工程师、产品经理

晨然对影像创作有着很大的兴趣
在2022年,GPT刚出来的时候,AI这个行业其实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确定的一个行业。但正是因为不确定性,很多老手看不懂这个应该怎么玩,所以年轻人才有了机会。
我正好就是在这个不确定性最开始的节点就接触了AI,所以我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认知,积累更多的经验。
我本科在复旦学计算机,研究生去了康奈尔大学。其实我在本科期间,并没有对计算机可以干什么产生任何的兴趣,也觉得课上那些知识很无聊,因为那时候能做的应用都很局限,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当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职场定位是什么,就只是当一份工作去做。
直到GPT出现之后,我就发现它跟我之前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成了一个人类语言和计算机语言相互转换的中间的桥梁,也让我重新开始对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分析是一种机器学习技术,使计算机能够解读、处理和理解人类语言) 这些事情感兴趣。

晨然用AI创作的克苏鲁短片的时间轴,灵感来源于Billie Ellish的歌《CHIHIRO》
毕业之后,我其实拿到了Tiktok的转正offer,但因为想回国工作,所以进了国内的一家大厂。
进入大厂的第一周,他们正好想要开始做AI,但是当时只有我懂,其他人都不懂,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稀缺性的资源,机缘巧合之下,被分到了做AI的组,我作为一个不做AI的部门里唯一懂AI的人,得到了很大的资源倾斜。
但后来我发现大厂的氛围有点“有毒”,我所在的那个部门已经不再适合年轻人了,因为大部分是年轻人在给上面的人打工,而上面的人瓜分果实。所以我只待了9个月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大厂的title对外没有任何的帮助。对我职场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去认识更多优秀的人,而不再是在传统的职场路径上去校招、社招,然后一步一步地往上升。

在ComfyUI峰会上分享
外面的世界里,更多是以demo会友,而不是以title会友。当时我做了特别多的产品demo,也做了很多AI创意视频,因为demo认识了更多的人,它是一个正循环。我意识到我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公众影响力提高,把自己有什么能力暴露出来。
也是机缘巧合之下,认识到了现在公司的联创,聊了之后发现非常匹配,所以来到了现在的公司。
好奇心在我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发现身边很多人不用AI,是因为他们觉得没什么要问的,但是AI可以满足我各种各样的好奇心,我什么都可以问它,它现在就是我的一把手。
我很多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于好奇。比如高一的时候我就上网课把高中三年的数学、物理学完了,高二我又对物理天文感兴趣,就看斯坦福的网课学天文学。当时纯粹只是想学,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觉得好有意思,也没有拿出任何的成果来,没有去参加比赛,我最后也没有去天文系。
我一直很爱看电影,高三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CG视频,就开始自己学AE,做特效视频。上大学以后,开始学微电影,自己买了电影机,自己导演、拍摄、剪辑了毕业M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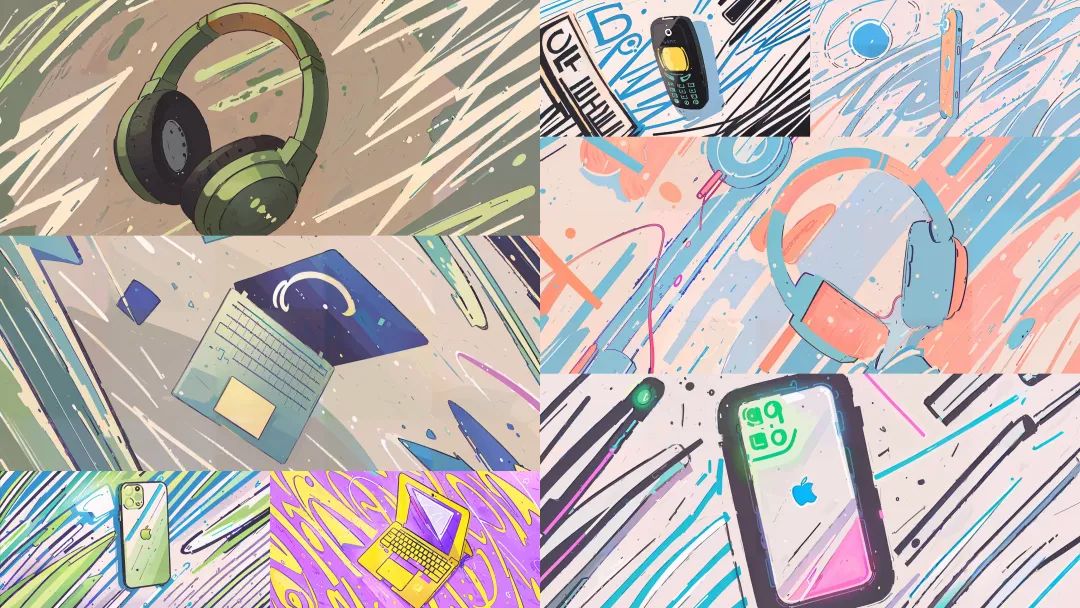
晨然用AI创作的短片《DEVICES》截图
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AI视频剪辑工具,类似于AI剪辑师。这份工作,正好需要的就是我过往已有的经验。
这个赛道或者说职业,在AI出来之前都不存在,以前的我不可能会预料到,而现在的我也不知道出了这个公司我还能做啥,恰好就有这么一个适合我的岗位出现了。你很难找到另一个,可以把视频剪辑和AI全栈工程师这两个Tag放在一起的人,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比别人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工具目前还非常早期,没有引起公众的讨论或者关注,所以日常我会自己去创作一些AI视频,目的大多是为了测AI视频能达到的边界在哪里。

晨然的工作日常
身处在AI的世界里,我会觉得AI带来了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的革命。
AI在我现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几乎已经占了100%,我的代码80%以上都是AI写的。
现在大家都在聊Agent(AI Agent,又称人工智能代理,是一种能够感知环境进行自主理解,进行决策和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实体),就是能自主完成某个任务、创新性解决问题的玩法,在每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中,都可以用Agent的形式去做一个自动化完成任务的类人的产品。
比如说AI自动剪辑,我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AI剪辑师,想要把它拟人化,是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能够类似于人一样去完成一件事情。你会认为它是一个实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工具,更像是你在用一个实习生。
当这些AI工具都加入到公司的生产环节中,人们将会更多聚焦于人的想法,而不聚焦于人的执行力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想象一下,一家公司只有一个人,聘了5000个大模型在帮他工作。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痴心妄想,这是一个完全可预见的未来。
非计算机专业,也能留在牌桌上
夹心 99年12月 杭州、北京
3D大模型公司海外社区负责人

夹心
我在一家AI 3D大模型公司做海外社区负责人,我们做了一个叫Tripo的3D大模型。关于“3D大模型”,从日常生活中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游戏、动漫来讲比较好理解,比如你玩黑神话悟空,或者去看《哪吒》,里面的角色都是3D的,我们在做的就是让AI把2D的图片或者一段文字变成3D的模型。
虽然算法目前肯定还没有那么完美,一定是没有《哪吒》那么精致的,但现在在全球我们已经是做得最好的算法了。
我们团队全职员工一共30多个人,最开始就是一群喜欢打游戏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喜欢用一个“老炮”加一个“小天才”这样的搭配组合: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学来提供一些方法论,更年轻的同学去做一些新的挑战。
团队里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年轻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跃升的机会,传统互联网的饱和度实在太高了,业务空间也不大。在大厂可能还是个小朋友的人,在创业公司可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们没有特别多条条框框,什么样的背景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比如我们一个运营的同学本科学的是生物学,也有资深的商务同事是从投资来的。
我在USCB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来到VAST,和团队一起做Tripo的海外社区运营。

夹心策划的活动:Tripo在圣诞节期间的活动,用户可以利用平台创作各种各样的“3D圣诞树”
有灵气、聪明和创业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大环境里大家可能都想考公,在我们这里,大家共同想做的是一个更厉害的产品,希望能因为自己的idea产生一些改变。
比如我们做的3D大模型,其实最开始它是个很小众的东西。 历史上从2D到3D这个过程可能非常复杂,你要学建模,学好几年,甚至交几十万学费来学,可能还学不好。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一键生成”成为可能。
我们Discord社区里的第一个创作者是哈佛的一个生物学博士,他本来是想用我们的产品试着做生物分子的结构模型,但后来发现做不到,他又很喜欢游戏,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游戏。
他完全是零基础,他既不是一个好的美术,也不是一个好的程序员,但是一个好的游戏策划,他就用我们平台完成美术建模的部分,用AI编程写Godot代码,最后很快做出了一个自己的demo。
这样陪伴着产品和用户成长的日子非常令人激动。

夹心参加Roblox的开发者大会
我们会接触全球各种各样的垂类社区,比如Roblox、ComfyUI等等。
做海外运营对我最深刻的一点其实是能接触到全世界的人。由于最早期从0-1地搭建整个社区,当时甚至和CMO一起每天没日没夜的跟和全球不同年纪、不同背景的玩家、创作者1v1建联。除了基础产品反馈之外甚至会聊到他们的国家背景和一些人生故事,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让前期这份看起来很“dirty”的工作有了灵魂。
我是深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做社区工作经常感觉挖到宝了。这个人是做电影的,给我引荐好莱坞导演推我们的产品;那个人是挪威AI爱好者但是是PUMA资深设计师,又将我带到PUMA官方的AI设计师群体。不知不觉感觉自己、自己家的产品就这么跟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挂上了钩。

夹心参加东京Comfy峰会
我们团队非常明确的一点是,进入这个公司,你是必须要使用AI的。我们内部有很多Agent ,有专门用来回邮件的、专门用来写方案的,也有专门用来做物料图的。写代码、做平面,几乎都会先用AI来打稿。
我 们社区和用户支持这个板块 , 传统意义上是相对 劳动密集型的,但现在我们几乎已经不写方案了,只会出选题,基本上所有策划都是AI先写,再一起讨论。
再打个比方,我们的Discord社区在全球有6万用户,他们是来自不同时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活跃度也特别高。而我们运营团队全职员工非常少,所以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在飞书多维表格接入了Deepseek的API,将用户的邮件和问题存档,进行自然语言分析和分类。
它不仅可以自动翻译,还会给我们一些小tips,建议我们如何去回复。这些留存下的内容都成为团队运营的知识库(或者进一步训练Agent的物料),帮助我们更加自动化和高效地服务社区和用户。
很多人会恐惧AI取代人类的工作,比如 平面设计 这类岗位。 但我 们 一直觉得 并且发现 ,因为有了AI,才有更多的人能来做 更多 创意和内容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称之为“empowerment(赋能)”。

夹心在亚马逊云科技中国峰会
我是Entp、射手座,我们运营团队的行为方式是三个“E”:Engagement,Experience,Exposure。对我们来讲,体验新的东西、探索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人接触,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毕竟现在AI是一个非常好的浪潮,这个时候能在浪潮里做出一些事情、能在牌桌上,已经非常开心了。

-
 C114通信网
C114通信网 -
 通信人家园
通信人家园


